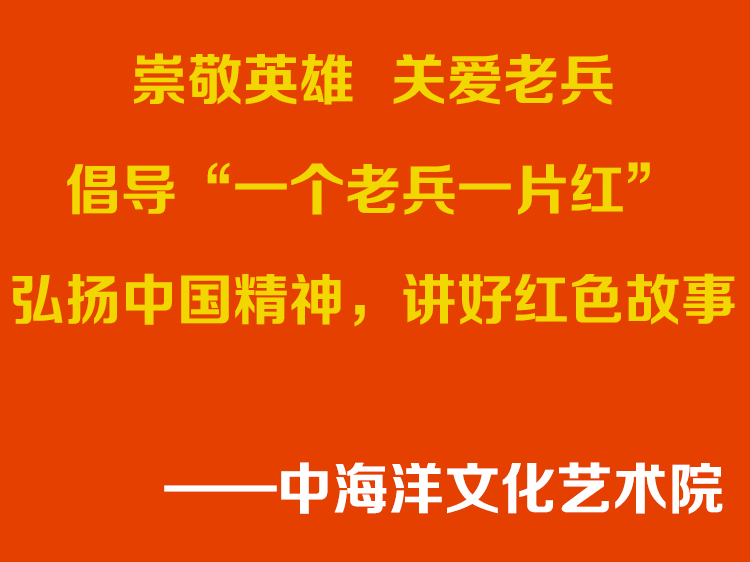分类导航
编者按:南凹年,不仅仅是因为她的贫穷、独特,更重要的是因为她的消失,因为她已回归沧海桑田!作者妙笔生花,把南凹年的消失原因写的绘声绘色,表达了对家乡的怀恋。
南凹年,已归沧海
渔兰
兔年,也许因为新冠的原因,七十余岁的亲家、亲家母的身体,时不时出点儿小状况,要么咳嗽,要么肺部不适,要么是孙女在校园带回来一点病毒,三个人一并咽喉疼痛、发烧不适!这一年,我因为出版《幸福黄河序章》和参加《山西黄河志》资料收集,离开京城先后在“豫鲁晋”居住了三个多月,这是我退休十年中,出门最多的一年。
年前,儿媳特地把一年的假期,移到孙女度寒假的日子里,带着她们到西双版纳那个完全不同于北方气候的环境里去住了几日,她们的身体在那种亚热带气候中明显清爽起来。
走前,她们约我一起去,我曾去过两次,便谢绝了她们的邀请。其实,我没去的真正原因是,本年度出门时间太多了,我反倒留恋坐下来,享受安宁静好,很有规律、跳跳广场舞、写写小文章的美好日子。
除夕,儿子安排我与大家一起到郊外去松散几日,说是过一个不一样远离锅碗瓢盆的年,对于老年人的身体和精神都会是很好的调理。我拒绝她们的邀请,我真心实意想过自由自在,静心写点儿小文章的年,但她们强调:这是年,是春节,不是平日里;中国人的年,是要团聚,要一家人一起,热热闹闹地一起过,才像那么一回事。
无奈,只好放弃自己的小打算,与大家一起到郊外过年。
我万万没有想到,她们安排的度假村,在距离密云水库只有18公里的水库区域中, 1997年我随水利考察团,从日本利根川河流回到京城时,曾参观了密云水库,一晃 27年过去了,能再一次来到这里,彷佛故地重游给我带来一份额外惊喜!还因为密云水库诞生与发展的历史,牵动着新中国开创者的战略谋划与发展,牵动着一代人对水利大型水库的创建、认识、管理应运,等等,总之对于一生从事水利事业的我来说,有着一份特别的亲近与温馨的感觉,在这里走走步,爬个小山,看看夜景,很是惬意!
无疑,与儿孙们一起度过的这个轻松愉悦、且又再一次观看密云水库的年,是我人生中从未有体验过的、完全不一样的一种年味,但夜深人静,可以游入我梦境中的年,根植于记忆深处的年,依旧是“南凹年”。
我用如下篇幅记载儿时的年,不仅仅是因为她的贫穷、独特,更重要的是因为她的消失,因为她即将连同那片沟壑丛生的土地回归荒芜,回归沧海桑田!
我学着走路时,父亲病逝,不识字的母亲很厌倦县城,她认为城里人多事杂,纷纷扰扰,总没个消停的时候,正是这些应酬不完的事与看不完的病人,把丈夫累死了。

父亲病故后,母亲带领我和二姐开始“倒退”,从县城回到条山北麓的南凹故里,后来我在诗文中称这次“倒退”为母亲的“二次革命”。
因为南凹的存在,太特别了,她不是镇,不是乡,实际上连个村名也没有,按照地壳形成的天然状态,从古到今,周边的人都管这里叫南凹,而不是叫南凹庄,或者南凹村,因为南凹就是南面坡后的沟壑凹地。
南凹很可怜,没有任何名气,它从来没有在版块地图上标示出来过,但走出南凹的前沟与后山,便是名副其实、叫得响的华夏民族根祖文明区域。
前沟,一溜下坡向外延伸三华里,便是汾河支流——浍水岸畔,《尚书》《山海经》《水经》记载中都有她的存在,郦道元《水经注》中,专作《浍水注》。康熙四十七年《桃花扇》作者孔尚任修定《平阳府志》时,将《浍水注》采入志中,读罢令我肃然起敬。更有趣的是,2023年我参加《山西黄河志》资料收集时,离退局艾薇科长,听到我的讲述,居然在网络上搜索到今存于美国大学图书馆的康熙版《平阳府志》,足见浍水在文化源头,不是可有可无,名不见经的一般溪流。
岸边有一条峻峭的青石板坡,小时候每逢跟着母亲去坡下的河北供销社,只要走到这青石坡头,我总是小心翼翼的,猫腰下移,担心若是摔倒了,一定会滚到河边的古圈门处。古圈门上方砖雕 “山明水秀”四字,正面雕刻有“古尭都”三个字,这里是“尧舜禹”原始时期,尧王建都前的唐尧封地。顺着浍水岸是南坡村与河北村,共有上千户人家,其中张家属于大户,有寺庙、族谱、族长与祖坟墓碑石雕等。
后山,则是出了院门顺着“之”字形小道爬上垣头,顺着山梁向南台伸大约20余华里,会进入原始森林、登上条山之巅——“舜耕历山”的舜王坪,《平阳府志》记载这里是“舜”年轻时期“躬耕负夏”之地;沿坪顶一围下方至今保留着一万余亩原始森林,是整个北方地区稀有森林区域,林中有豹子、金丝猴、山猪、麝、娃娃鱼等等,有松、杉、桦木等等极为丰富的植物种类;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植物研究所长胡小平,带着一支武警小分队,在其中采集到25种原始森林特有植物标本,填补了历史空白。
南凹有着如此之地理位置,今日听上去,很有根基厚重之美,尤其随着经济日新月异,条山顶的“舜王坪“已被来自三个方向的地市县乡,熙熙攘攘地开发名胜起来了;三个方向的旅游路、高速路都延伸到了“舜王坪”四周,但是在“条山战役”后的建国初期,这里的日子可谓苦不堪言,而寡母支撑的日子那便是难中之难!
最初的南凹,只有张姓一户人家,曾经担任条山战役民兵医院院长的父亲,在条山转战时,结识了宋家、赵家与另外两户郭家朋友,他们在建国前迁移下山来到这里,尽管如此,南凹总人口从未超过百人。
除去一座完整的四合院落外,余下均是削切土崖、人工开凿的土窑洞院落,每个院落平台皆不足50平米,余下的空间全部是沟壑山梁,梯田洼地,荒野茅崖,出了院子不是上坡,就是下坡,挑水要到沟底里去,种地要到梯田和垣顶上去,在这里的生活与生存,最基本的功力一是挑,二是扛,三是推磨碾米转圈圈,若没有此不惜出力流汗的三大本事,便无法生存。
母亲是张掖人,姥姥早年去世,姥爷是位小商贩,她从小没有接触过土地,没有耕种收获的经历,父亲走西口时带母亲回到故里时,母亲小父亲十余岁,抬手动脚依赖父亲。
父亲是位秀才,教书、行医、种地都很在行,去世时,任县人民医院院长,那时大姐刚读高中,哥是初中。他知道妻子不识字,在县城带着几个孩子很难生存,病危之际反复叮嘱母亲:“我走后,你带娃们回老家,山里有地,遇到旱年景也饿不死人。这个社会,多穷都让娃们读书,不管男娃女娃,读书就有出息,以后咱大女肯定比儿子强些。”
父亲的话很灵验,五十年代末,大姐考上了山西大学哲学班,哥考取了长春滑翔学校。
不识字的母亲,验证了父亲所言不虚,在其后的寡妇生活中,无论日子过的多么贫困悲惨,甚至在青黄不接、扫瓦罐断顿时期,她东讨西借,求爷爷告奶奶,都没有让我和二姐的读书停下来。
我和二姐因为母亲的这点先进性,逃脱了南凹人祖祖辈辈、天经地义的男尊女卑法则。
“读书就有出息”是母亲的坚强信念。“看你大姐,进了省城就是出息了”,母亲时时举起大姐这块靓丽的招牌,教训和教育我和二姐。
大姐的出息,成了母亲的荣耀,也成了我和二姐的目标与榜样。我和二姐也没有辜负母亲,在土窑洞四个年级共一堂的“复式教学”模式下,考出了好成绩。我最早一次令老师骄傲的好成绩是“全镇汉语拼音第二名”,那次参赛前,为了保存体力,在通向镇上一节陡坡路上,年轻的尹开昌老师背着我爬上去,我小时候性格强悍,告诉老师“我爬坡很厉害,比我二姐快的多”,老师说“我知道,我是怕你饿了,关键时刻记忆减退。”后来走出了大山,才知道,我的汉语拼音几乎将全部的“en读成了eng”、“yin读成了ying”、“yun读成了yong”等等,但我的老师却因我和二姐的优异成绩受到表彰,终究被调整到镇上高一级的学校去教学。
我们也没有辜负母亲,我升五年级那一年二姐考入了县重点中学,我读六年级的时候,班主任老师爬过两个山头家访见到母亲,得知我在如此环境与教育中成长,向校长汇报后,我便由中队长晋为少先队大队长,当然除了学习,老师们与校长也看清楚了我“能挑能抗肯干活不懒惰”大自然赋予的本事。
六十年代初期,大姐大学毕业,分配省政府工作。她工作很忙,平时很少回家,总是姐夫替代她回家看望母亲和我们。但每逢过年,大姐和姐夫才会一起回家,住上几天。姐大我16岁,大二姐14岁,她从来不与我和二姐一起玩,也没有给我们买过什么玩具新衣服之类,只记得她给二姐买过一块“镜子石板”,待我上一年级时二姐就让给我,那是我在同学们面前最能说起嘴的一件稀奇东西。她总是陪母亲说说话,把积攒下的一点钱交给母亲,母亲总会说“你婆婆也是个寡妇,日子不容易,也记着给她留点”。姐体质不好,经常生病,她能留给母亲的钱肯定不多,我知道有一年春节过后不久,母亲便叫来三个小伙子,把后窑下面地窖里老辈们留下贮藏粮食的两口大缸拉出来买了二十余元,买回半袋“返销粮”玉米。
哥也很少回家,每逢过年,只要哥回家来了,那个年就会变化出完全不同的味道来。
因为哥一回家,家便顿时热闹起来,他是山凹里的明星,一帮同龄人很快会聚在他身边,听他讲外面的世界,听他唱歌。这山凹里不知从何时起,有一个每逢过年必搭丈余高秋千的传统。
秋千的高龙门架子是由两根很高的白杨树来做,顶部垂吊长长秋千座板的横杆则用槐木来做,横杆与竖杆的连接处,要拉起东西南北四根长长的绳子,用以保持秋千整体的安全稳定;当整个架子与绳索全部拴好就位后,要集中南凹全部男劳力一起喊着口令统一行动,将捆绑好的龙门架子连拉带抬,置放到两个很大的碌碡上去,然后拉紧固定好四根不同方向的绳索,一切就绪后,总会有一场不是竞赛的竞赛,大家会远远地围成一个大圈开始评论“谁谁荡得最好、谁谁荡的最高!”
自从哥成为滑翔班的学员后,全村老少没有一个男子汉能荡出哥的水准来,每逢他荡至丈余高与龙门顶横杠齐平时,围观的小伙子们就会起哄高喊 “船儿,船儿”,那是哥的小名。这时候,哥的身体悬在高空,轻如飞燕,他会紧紧抓住与横杠起平的那一瞬间,双手快速、大幅度抖动手抓的长长吊绳,带动拴在横杆中间的铃铛激励碰撞、发出清脆响亮的声音来。
每逢这时,也是我和二姐最得意最为骄傲的时刻,比自己考了百分还要高兴,仿佛我们也顿时英雄起来,便对伙伴们大声炫耀“全南凹的人,谁能荡过我哥!”
还有一次,初一下午,赵家小个子老二,因为去供销社买煤油回来,被南坡几个小子欺负的连油瓶都摔碎了,她母亲气得无处出气,用笤帚打了他一顿。他知道自己个子小,就是与他哥两人去还是打不过人家,就跑来向我哥求救。
哥便拿上镰刀与他去后山选紫荆木做弹弓,最终教会他打弹弓,后来他用弹弓战胜了南坡那群小子,再没有人敢欺负他是个矮个子。
哥还教会我和二姐做很漂亮的公鸡毛毽子,他一次能踢三百多下,我们踢了很多年,终究未能突破他的记录。每到除夕下午,哥会带着全院的小伙子砍来柏枝,背来一捆捆高粱玉茭谷子杆,在院心堆起一人多高的“年年火”,柏枝是摆在最上面的。
大年初一黎明时刻,喊全院的孩子们,穿上新衣服,围拢起来后再点燃。当火苗超出砖窑顶时,柏枝燃烧后的声音与香气,与大家的呼喊声,会顿时令院子里的年味上升到顶峰!
那年景,南凹一个全劳力一日争10分工,到年底分红,这10分工多则2毛五分钱,少则6分钱,年底大人们根本舍不得拿钱买鞭炮给孩子们玩。有时候,大家会到地里找来粗壮湿润的玉茭杆,剥掉叶子,从前面三分之一处折一下,然后围着碾盘一周,去甩出“噼噼啪啪”的响声来,替代鞭炮声。只要哥回来,他会用自己在学校积攒下的津贴,买回两串鞭炮拆开,分发给伙伴们,大家很珍惜地将小鞭炮装在口袋里,慢慢地燃放!我和二姐很喜欢有哥在身边的年味!
后来,我和二姐中学毕业,虽然赶上了十年不招生的特殊年景,且终究因为读书而双双走出了南凹。
二姐成为中等专科学校的英语教员,我成长为一名水利工程师,我们先后在都市里成家立业,过上了与南凹完全不一样的日子。但是母亲,一直铭记父亲的嘱托“守着南凹土地,遇到旱年饿不死人”的理念,坚持不离开她所耕种的土地,我们只能每年轮流将母亲接入城里过年,到了春天,再送她回家耕种土地。其间,无论我们怎样向母亲保证,城里的供应粮食一定不会断顿,母亲还是坚守自己守着土地的踏实信念。
再后来,我将离岗时,在省厅为南凹申请到一份“贫困山区人兽吃水打井经费”,万万没有想到,批复文件拿到大队支部书记身边时,河北大村因为开采煤矿泉水底漏,千余口人吃水面临困难,连浍水河里的水也渐渐干枯起来,于是这一份经费终究产生了一个令我做梦也想不到的结果:南凹人全票同意支部决定“搬离南凹”,或合并南坡村与河北村,或投亲靠友。
再后来,72岁的母亲因肾功能衰竭在市人民医院医治无效去世。
从此,南凹与南凹年便开始渐渐远离我们,但迁离南凹的人在耕种季节,还会回到这里住些日子,每逢清明节气,我们也会到南凹垣头的坟地里,为母亲祭祀上坟,虽只有几个小时的停留时间,只要相遇南凹的伙伴们,我们还会一起津津乐道地讲述南凹的人与事,讲述完全不同于外面世界的“南凹年”!
后来,渐渐地,我们回去的越来越少了,但是,每次回去,我们都会到院子里、窑洞里转一转,看一看,念诵一番。花甲年我正式退休,跟着儿子住入京城,2019年中秋节,我再一次回到南凹,这里的情景令我大吃一惊,映入脑海的第一感觉是“沧海桑田”四个字!

四合院里的门窗已被卸走,堆积下厚厚的泥浆,生长着齐人的蒿草荆条,窑顶上的酸枣刺与紫荆条长长地垂落下来,遮去了窑洞上的天窗,若是再有几年时光,这里一定是一个完全的动物世界。
在母亲坟头祭祀一番后,我到搬迁至南坡河边堂哥家时,那是一个崭新的院落,可以看出他们的日子比在南凹时一点不差,堂哥告知,现在散落在各处的南凹人除去一两户家里因病与车祸外,能吃苦的南凹人现在都过得不错。
如今,年入七十,满头华发的我,对生活十分满足,但不愁吃喝穿衣的幸福年,却依旧替代不了南凹梦与南凹年!南凹年,已伴随那片沟壑,归入沧海!我唯独梦里,可以亲近这“南凹年”!
二〇二四年二月十三日正月初四燕山密云
作者简介

张志坚,女,现年70周岁,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退休前,任黄委会山西局水利高级工程师。现为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红学会员。曾出版《感动黄河》诗集、《河图》连续剧本。《百年黄河之子》散文集,与《另说红楼》《红楼梦真相揭秘》和《另解红楼梦》著作。近期创作长篇纪事文学《幸福黄河序章》,已交付“黄河水利出版社出版”。